


走下讲台
杨玉翠气炸了。
新一学期的分班结果,完全在杨玉翠的意料之外,她本该继续带三年级,现在她的名字后面是两个刚升二年级的班,这两个班平均分倒数,谁也不愿意教。
后来,杨玉翠诙谐的称他们为“小魔王”,一开始的小魔王当然不可爱,调皮捣蛋,扰乱课堂,老师讲得再详细,坐在下面的学生压根没在听。
杨玉翠意识到,步要解决的不是本节课讲述哪些知识,而是如何组织教学。
那时候没有“站在儿童角度”这样的理念,但是杨玉翠为了解决问题,主动观察起了儿童。她发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孩子学会倾听,她又注意到对于低年级的孩子,收集卡片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。根据自己心目中认为孩子应该具备的素养,杨玉翠的一套卡片诞生了:大耳朵卡片代表会倾听,心连心卡片代表会合作,问题老爷爷卡片代表会提问题,小老虎卡片代表大胆发言……班里每月评选一次“数学小明星”,每学期评选“数学小博士”。杨玉翠管这个叫作“数学素养储蓄银行”。小卡片越多,说明这个数学素养积累越多,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孩子一个正面评价,同时帮他们找到上课的乐趣。
卡片一出,课堂转变巨大,但课堂的实质形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,老师依旧占据着讲台,杨玉翠觉得这样不行,面对自己的班级,杨玉翠是局中人,找不到突破口。而当她成为一个旁观者,一件事情给了她极大的触动。
那个叫小方的孩子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额外辅导,这天老师中途被叫去开会,把小方单独留在办公室。这个孩子拿了老师刚买的枣子就跑掉了,恰巧被回来的杨玉翠看到。“老师辛辛苦苦为他付出这么多,为什么孩子一点都不领情,相反还对老师充满了仇恨呢?”杨玉翠在这件事中不断反思:到底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呢?
在反思中,杨玉翠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,一次上课,杨玉翠叫醒了一名在课上打盹的孩子,她没有批评孩子,反而想“那不如让孩子自己讲讲题吧”。杨玉翠发现,孩子在讲的时候,教室氛围很不一样,大家很安静并且注意力十分集中。
那以后,杨玉翠开始尝试让孩子上台当小老师。一开始上台的孩子当然很紧张很害怕,语无伦次,但是下面的孩子却非常兴奋,也不打盹了。杨玉翠开始“开小灶”了,她先教那些学得好的孩子如何做小老师,不断鼓励他们。小老师们在台上发挥得越来越好,到后来,轮值的小老师会早早地在学校门口等杨玉翠到来。
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,杨玉翠找到了职业成就感。
回望六年前,刚毕业的杨玉翠天去学校入职,那天大雨,她踩在泥泞的路上,远远看见破旧的学校围墙,她想:在这里干满三年,我一定要逃离老师这个职业。尽管初次站上讲台的杨玉翠就如鱼得水,尽管她所带的班级数学永远名列前茅,这个想法从没变过。
三年又三年,她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,从初中到小学,最后,在自己闭上嘴巴、走下讲台、倾听学生的声音后,开始笃定教师这条路。
相互成全,无外如是。

从60分到80分不难,从98到100却是一个陡峭的悬崖。
生来不爱循规蹈矩的杨玉翠,似乎注定要遇见职业路上的陡崖。2007年,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小学数学教研员张爱玲对她说“你敢不敢把课堂再放开些?” “我先在小班试试。”“不,两个班一起做。”她们一起站在了陡崖边上。
课堂的主导权开始更大程度交给了学生,学生自主预习,产生问题,研究问题,做小老师讲解问题。为了这场实验,2007年的杨玉翠花4000块买了一台电脑,白天黑夜地设计学习单,回想起那段日子,杨玉翠连用了六个最来强调,那是人生中最累的半年。结果却是,两个班的成绩从正数一、二滑至倒数一、二。
一向乐观的杨玉翠懊恼不已:我费这么大劲,何苦来着?一向坚定的杨玉翠产生了自我怀疑:还要继续吗?一向自信的杨玉翠自我否定:麦当劳和肯德基也是孩子喜欢的,但它们是垃圾食品啊!
陡崖还攀不攀?
张爱玲对杨玉翠说:我和你一起再尝试半年。杨玉翠记得很清楚,班里有个脸蛋黑黑的孩子,学习很弱,在学校这孩子几乎都撅着个嘴,杨玉翠的课堂开放以后,孩子们自发地给他当小老师讲题目,比自己辅导还管用,那阵子总能看见小男孩露出白白的牙齿,一脸笑容。
“成,再试半年。”冷静下来的杨玉翠开始分析原因。
课堂出现的问题很多,比如自己只需要20秒钟就能讲清楚的地方,学生5分钟都未必能讲明白;学生自主预习就会有五花八门的问题,又不能无视孩子的问题,讨论问题的时间一长,留给学生练习的时间就少了。
“方法是好方法,问题在于课堂效率,在于我对课堂节奏的把控。”杨玉翠的自信又回来了,她对“小老师”们开始提出要求,根据不同难度知识点设置不同时限,先来给她预讲,时限内讲不清楚,就不能做本次小老师。然后记录孩子们课堂提出的问题,进行分类,哪些问题是本节课的共性问题,哪些是进阶问题,哪些可以放在课后讨论,哪些先哪些后,不再是碰到什么问题就一定在课堂解决什么问题。
“我还特意买了本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书。”杨玉翠笑道“每天我就观察学生行为,有的能和书中的对上,有的书上没写,没写我就去找学生聊。”杨玉翠那时的想法很朴素,就是想多了解孩子,看懂他们语言背后的意思,从而调整课堂。
调整之后,学生在课堂“百家争鸣”之时,节奏也渐入佳境。半学期后,两个班级成绩又重回正数一、二。
“杨玉翠的课堂不是她的课堂!”时任淄博市基教科科长的李传英听完杨玉翠的课后,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叫庭庭的小姑娘失踪了,老师以为孩子在家,家长以为孩子上学了。
庭庭也算是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,原因是这个小女孩太慢了,一个题目跟她讲很多遍问她会了吗?她说会了,用不了半个小时,再让她做,她又不会了。
当天晚上,不知道在哪玩了一天的庭庭自己回到家。家长气到不行,斥责孩子为什么逃学?第二天,庭庭来到学校,毫无意外地被班主任找过去又是一顿教育。
家长老师都在生气,庭庭在哭泣,不知道出于什么契机,杨玉翠问庭庭“你为什么逃课?”庭庭泪眼汪汪地回答“老师我很累,我想休息休息。”“为什么很累啊,是晚上睡不好吗?”“我不明白题目为什么这么做,你们就跟我讲,过一会我忘记了,你们就批评我,我就特别害怕,特别累,学习太吓人了,我就想休息休息。”
这是杨玉翠更大的困惑:如果孩子真的不擅长学习,或者不擅长某门课的学习,该怎么办?
直到2013年,杨玉翠离开淄博来到北京遇上全课程,这个困惑才终于被解开。
和杨玉翠以前的课堂的不同是,全课程是包班制,包班老师整天都待在教室,换言之,孩子一整天的状态都被老师看在眼里。
这给了杨玉翠研究儿童这个“神秘群体”更好的机会。
一天天观察下来,杨玉翠发现了问题:以前的孩子是分裂的,老师评价孩子也是分裂的。因为清晰的学科划分,数学老师只知道孩子在数学课堂是什么样的,离开了教室,就不知道孩子的其他模样。而孩子本身,可能在语文课上积极活跃,被老师喜爱和表扬,不擅长数学而得不到成就感,最后发展为严重偏科。
而如果老师一整天坐在教室,就能看见孩子更为完整的样子,他的劣势优势,兴趣所在。
杨玉翠班级里有一个小女孩数学很差劲,换成以前,她一定要额外给小女孩补习了。但是杨玉翠见过小女孩跳舞时候的样子,美得像一个天使。一道数学题,女孩得很久才能学会,但是一个舞蹈动作,女孩看一遍就会了;花一个小时练习数学,她肯定叫苦连天,但跳上三四个小时的舞蹈,女孩也不觉得累,反而快乐得不得了。
“人是靠自己的长板活着的。”杨玉翠自嘲“板书差、普通话差、形象差”,但是她极度清楚自己擅长讲,她就是靠这个长处一点点走成如今的杨玉翠,那么为什么非要一个孩子什么都要达到呢?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逼孩子去做不擅长的事情呢?为什么不让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在擅长并且喜欢的事情上呢?那个不擅长的方面只要达到标准就好。
杨玉翠看见的儿童越来越完整,困扰多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散散出生于艺术世家,在父母的熏陶下,打小便十分喜欢绘画。但是他不喜欢数学,杨玉翠对他的标准就是,能够达到标准并且不讨厌数学。
如何做到不讨厌数学呢?给他成就感。
有一次散散提了个问题,杨玉翠立马夸奖道:艺术家会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数学,你提的这个问题多么有艺术味。画三视图的时候,杨玉翠对散散说:美术和数学是不分家的,为什么?比如咱们现在要观察物体画出三视图来,这和美术是不是一样的?所以你可以成为“数学小画家”。
散散很喜欢这个称呼。
后来,杨玉翠不教散散数学了,他对数学依旧没什么热情,但他并不讨厌数学老师,也并不讨厌去学习数学。
“这就够了”在杨玉翠看来,“他健康地找到喜欢的东西,每个孩子都这样,社会不就好了吗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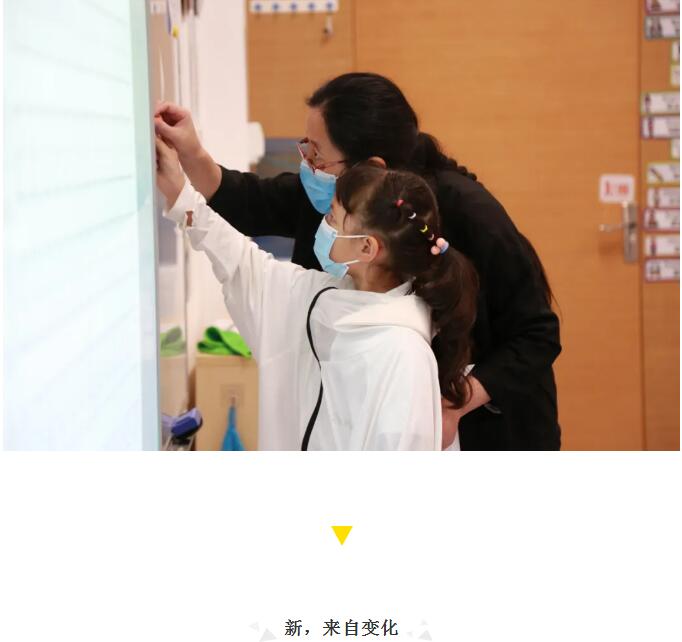
杨玉翠很享受现在的生活:每天都是新的,每天都有惊喜,生活特别多彩。
每天究竟有多新?
这天杨玉翠一进门,用夸张而抑扬顿挫的语调说:我看谁把自己的大脑调到了数学频道。孩子一听,多么有意思的一句话啊,一下子就被吸引了。这还不够,杨玉翠接着说:谁谁谁的眼睛亮了,大脑已经调过来了,谁的大脑还在语文频道,快调过来。哗哗哗,这下所有孩子扬着笑脸全部被杨玉翠吸引了。
当许多老师发现这样一句话的效果很好时,往往会使之成为和孩子之间约定俗成的东西,帮助快速拉回孩子的注意力,杨玉翠却不,她要琢磨出千变万化的语言,让孩子每节课都能感到惊喜。
第二天,她刚说出“我看谁”三个字,有孩子立马说“老师我知道,谁把自己的大脑调到数学频道。”杨玉翠迅速反驳“不对,我看谁昨天很帅,今天不帅了呢?”学生们又轰然一笑,看着孩子们的注意力全部在自己身上之后,杨玉翠接着夸赞道“现在男生都很帅,女生都很漂亮。”
很多去听杨玉翠上课的老师,最后都成了老杨语录的忠实粉丝。
孩子们每天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对问题的思考,也是杨玉翠无穷快乐的来源。
在数对的学习中,比如数对(2,3),2代表第二列,3代表第三行。有同学发现电影票上的位置正是数列的运用,但是却是先写第几行,再写第几列。进而又有学生指出火车票也是先行后列。质疑便产生了:数学为什么这么别扭呢?为什么不和生活中的应用一致先写行,再写列呢?
杨玉翠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,在此之前她没有发现这个不同更没有思考过,于是习惯隐身的老杨只能在万众聚焦之下回答: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!可惜,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坐标系是数学家笛卡尔发明的,他在规定的时候,可能有他的道理。
但这个质疑却有重大意义,杨玉翠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学生在数对学习中总出现行列写反的错误,原来是和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相关,这样一来,反而帮助学生规避了这个易错点。
还是这堂数对课,有孩子问:为什么数对要用括号,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用逗号,不用分号、句号,或者冒号呢?
在传统意义上,符号的问题属于语文的范畴了,杨玉翠在听见这些问题时突然意识到:单纯一个数学老师已经很难应对学生的问题!时代呼唤全课程老师!杨玉翠一个数学老师更是教起了孩子画画。
她把一组立体物件摆上展示台,然后让孩子画。孩子看了半天问她:怎么画啊?杨玉翠伸出一只手,作出向物件拍去的动作:你一巴掌把它拍扁,拍扁以后它是什么样子,你就画什么样子。
这其实是杨玉翠对孩子空间能力的训练。在上图形与几何知识的时候,她发现那些平时喜欢画画的孩子空间思维能力特别好,她就去美术室研究,发现画画就是三维二维不断转变的过程。这可不就是空间思维的培养吗?还有动手做东西也是一个道理。杨玉翠越发明白了全课程“打破学科壁垒”的意义,学科与学科之间,本来就不应有界限呀!

QCC课堂这个名字,源自杨玉翠和当时的搭班老师纪现梅的讨论,最后发现,做了这么多年的课程,无外乎是三个关键词:问题(Question)、对话(Conversation)、合作(Cooperation)。于是就取了这三个英文词的首字母,作为自己的“教育名片”。
她的学生曾猜想数学家是如何发现一系列课题的:“在他们还不是数学家时,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很多难题,然后他们就提出问题,再搞一个小组慢慢讨论,讨论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,再联想到别的东西……”学生的猜想,或许是对QCC课堂最直白的解释,这个直白的解释听起来有一点初生牛犊的大胆, 但杨玉翠听完立马鼓励:真棒,你已经有联想的本事了。
杨玉翠的课堂永远从问题开始。
“请同学们打开课本,看着目录,你想研究什么问题?”没错,她的数学课是看似枯燥的目录。
孩子们却一下子被这样一个开放性问题打开,在孩子眼中,文字生硬的一条条目录仿佛变成了陈列柜里琳琅满目的商品,他们津津有味地一件件浏览,挑挑选选。
每个孩子挑选的问题和理由当然各不相同,分享的热情使得他们相互展示自己的“商品”,师生和生生之间不断产生对话。
杨玉翠很少发表自己的观点,她不断提炼着学生的观点,不断思考着如何把学生“卷”进每一场对话中,并在合适的时候将思考推向下一个阶段,当然还是用一个个问题。
依然是这节目录课。
生1:我对运算定律这个单元感兴趣,因为以前没有学过,我猜测这部分与计算有关。
生2:我觉得用计算器探索规律与数和计算也有关……
顺着这两个孩子的对话,杨玉翠立马提出问题:是不是想用分类的方法研究这些内容?于是课堂的第二个任务就出现了:给目录中的知识分类
分类方式层出不穷:与图形相关,与统计相关,与综合实践相关……

杨玉翠不是课堂唯一发出问题的人,学生的问题会比她还多。
有学生问杨玉翠:为什么要用分类的方法思考问题呢?
回答他的是却是学生:思路更清晰,学会了一个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和它同类的。
杨玉翠也有问题:为什么分类就更清晰呢?
问题一个接一个:有没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呢?
回答他的还是学生:可以按照学过的和没学过的分类。
杨玉翠也要接着问:这类分类方法有什么好处?
答案还是学生给的:用以前学过的旧知识解决今天的新问题。
课堂被推向下一个阶段,学生纷纷献上“如何学习新知识”的办法,并开始相互学习。
合作就这样发生了。杨玉翠从来不担心激不起孩子的兴趣:问题都是孩子自己提出来的,课堂都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,孩子怎么会不踊跃呢?
在这样充分的讨论之后,整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已经在学生心中有了清晰的框架,接下来就是给框架添上枝枝叶叶变成一片森林!
在课堂中,杨玉翠总是很少说话,多半时间都在隐身,她隐身的方式就是变成学生,变成一个很好的听众,偶尔上线“混”在众多“问题”学生中,抛出自己的问题。当老杨隐身,课堂的主角才会变成学生。
一次,全课程实验校请杨玉翠去上示范课,安排了一个大型礼堂。杨玉翠不愿意了,一定要换成教室:我和学生隔这么远怎么产生对话,怎么听见他们的声音呀!一旦老杨不能隐身到学生中了,似乎不会上课了。
杨玉翠一贯认同“知识不是教师传授的……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能力。”这个观点,所以她认为教师的作用,就是设计好能够引发学生思考的问题。很多时候,问题不需要杨玉翠问出来,这是她最想看到的课堂:学生能自己提出问题。隐身的老杨并不是下线,不说话的老杨比发言时更加敏锐,一双耳朵里听见八方声音,一双眼睛看见所有的学生,精准地把握着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和对话。
每次公开课之后,总有老师问杨玉翠,你提前知道学生的问题吗?在几个学生的问题之间,为什么先解决某某的问题?
杨玉翠永远都是和课上的学生同时知道学生的问题的,先讨论哪个问题都是她当场决定的,而她的决定源自对学生的判断:深度(难度)是否合适、是否感兴趣……
只要学生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,老杨就会悄然隐身,把问题扔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讨论解决,然后以讲座或者授课的形式教会别的学生。
有老师问:如果学生打开的幻灯片,不是老师想要的,怎么办?杨玉翠回答:“只要是学生的真实状况都是我最需要的,我的任务是以学定教,而不是让学生去猜测老师的思路。正像斯苗儿老师说的,要顺着学生,而不是逆着、绕着、躲着……”她并不害怕课堂出现“失控”。
杨玉翠经常被类似“人们是怎么想到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°的”这样的问题问倒,学生不会因为杨老师回答不上来而看低老杨。杨玉翠自己说:“对于学生,并不是我比你大、我比你强、我比你聪明、我比你全面,学生就尊重我。有时候装点傻,学生反而和我越更亲近。当然,有时候是我自己真的‘傻’。”
杨玉翠想要的不单单是这份亲近,而是她的孩子们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,说出自己的想法,不畏惧权威,不人云亦云,敢于向老师向教材挑战。杨玉翠称之为:真正的勇敢。
在学习乘法时,有一道习题:图中三种面包和四种饮料能搭配出几种组合呢?杨玉翠发现了错误答案9,她哈哈笑着说:你们做错啦。但是后来,她发现学生们的答案竟然都是9,一问学生为什么,学生回答她:因为矿泉水不是饮料,那3乘3不就是9吗?
杨玉翠恍然大悟,并立马反思:数学知识在应用过程中,还需要生活经验。同时她也欣喜于孩子们的错误答案,错误答案背后体现的是孩子对“合理”性的思考,是一种数学的严谨精神。
一位三年级的小朋友在做书本练习题的时候,发现配图的恐龙图片不对,并列出一条条原因。杨玉翠收到后马上查阅资料,也列出一条条原因并感谢他的指正。
所以孩子们跟老杨亲近,老杨包容他们犯错,他们也能质疑老杨,老杨完全走进了学生。

现实生活中,杨玉翠也不喜欢被众星捧月。
如今,杨玉翠身为北京赫德双语学校这所国际化学校的中方副校长,但她身上还是一种极靠近土地的气质,是邻家老杨,原始而质朴。
每当我们一群年轻人给她让开道路请她前面走时,她总摆着手像赶一群鸭子似的:你们走你们走。然后迈着步子隐在我们身后。
